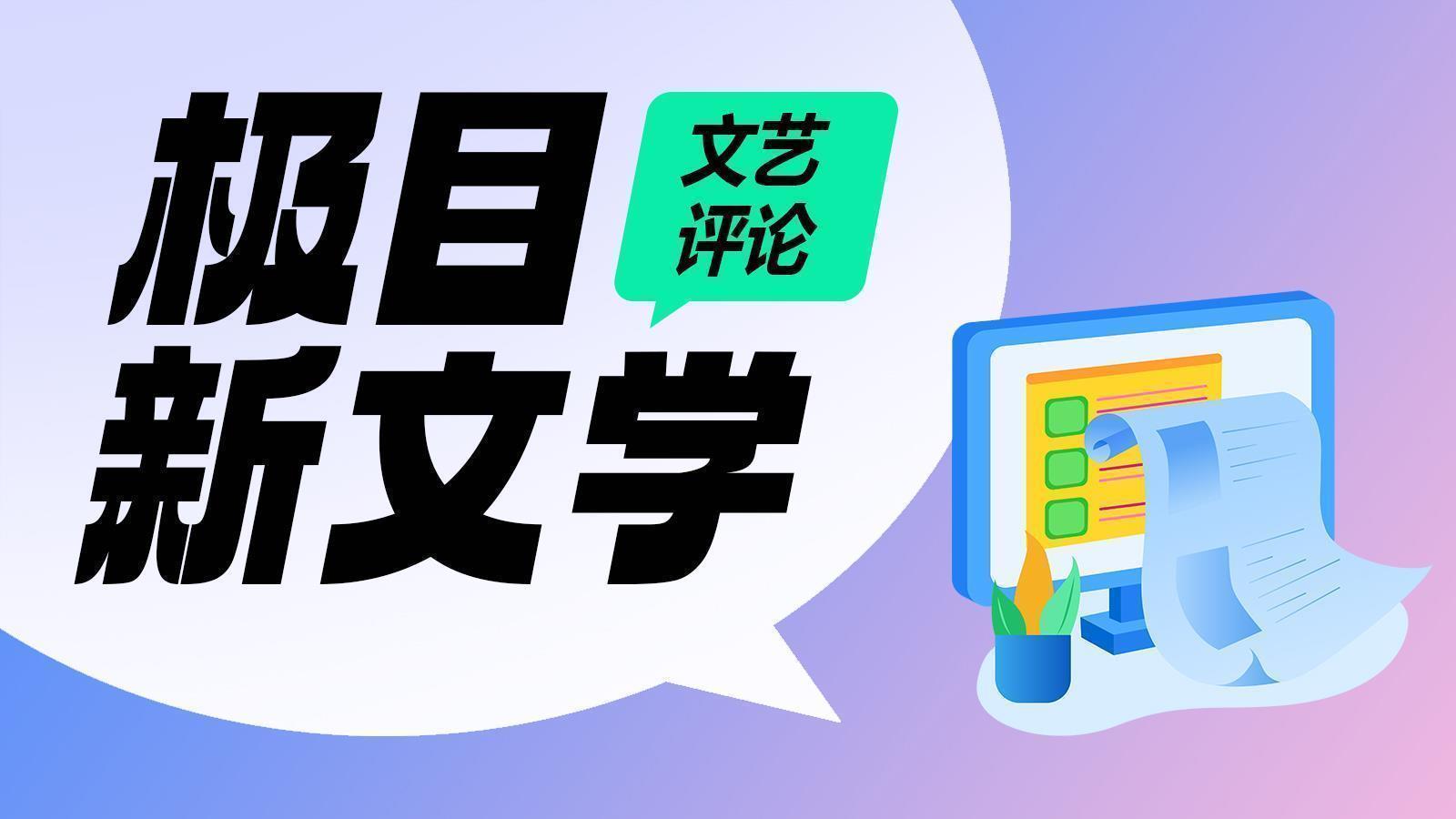
近年来,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科幻小说中的植物书写逐渐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对“人与植物融合”的想象经历了从“植物恐怖”到“共生想象”的转变。
理解这种转变,有必要回望思想史背景。
在中国传统宇宙观中,植物与人体都是“一气化生”的产物。“人以天地之气生”,“气”是贯通天人的载体;草木则因“天地至仁之气”“随时而发”,与人体同源,与人世变化同息相应。这一观念形塑了古典小说中的植物形象:自魏晋南北朝起,志怪与笔记小说记载了大量神异花木,兆吉凶、化形、助人或害人;唐代之后,“人植互化”题材盛行,在明清小说中达到高峰,《聊斋志异》《镜花缘》中草木精怪故事流传至今。
但是,经由西方近代科学的认知改造,古典文学中的“草木”成为了科学意义上的“植物”,从而在科幻小说里找到一席之地。19世纪后,以林奈分类体系为代表的西方植物学传入中国,植物被重新定义为可以被观察、分类、剥离本土文化语境加以理解的“科学对象”。命名与归类成为人类理解植物的主要方式,拉丁学名、形态测量与标本制备构成了获取植物知识的标准步骤。这无疑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看待植物的方式,也塑造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想象空间——“植物”被中国科幻接纳了,但是,被科学化、对象化的植物与人体的联系也同时被淡化了,植物成为人类的“他者”。
融合即退化:“植物恐怖”的机制
当植物被视为“他者”时,人植融合呈现出可怖的、令人反思的图景。如哲学家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指出,植物在西方思想传统中长期处于“哲学的边缘”,它们缺乏行动性、主体性与逻辑能力,因而被认为是进化链条中的“低等生命”。在这一语境下,科幻小说的人植融合所触发的是人对于“自身退化”与“失去人性”的恐惧。本质上,它催生的是人类对自身边界被模糊、被剥夺的焦虑,而非植物本身带来的自然威胁。
这一倾向在1990至2010年间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可见一斑:安蔚的《植物》(2004)将末日来临时人类接受“植物化”手术描述为“舍弃动物情感,接受永恒孤独”的过程;赵永光《植花演义》(2002)将人体植花实验设定为消费主义催生的畸形商品;田肖霞的《花魂》(1996)和迟卉的《雨林》(2007)则将人化为树木视为主人公在追求更高生命价值时做出的牺牲。
最为典型的是湖北科幻作家赵如汉(笔名北星)的早期作品《绿星居民》(1992),该短篇小说初刊于《科幻世界》。在传统的太空探险故事中,绿色植物往往是外星球存在生机的证明,而《绿星居民》所在的星球,却遍布“令人感到死寂的浓绿色”。考察队最初观察近似“三脚树”的生物,得出结论“只不过是高等植物”。然而,飞船被“高等植物”瞬间腐蚀,主人公滞留绿星,并在意识中接收到来自绿星植物的问候:“欢迎你,新生的绿星人!”此刻,主人公还坚持着人类的身份认同,尚有警惕和排斥。但在四面八方涌来的意识洪流中,植物的反驳和劝说让主人公逐渐动摇,甚至接受了与绿星历史有关的记忆。挣扎之际,绿星的“母树”为主人公注入“巨大、温暖的爱”,最终让他依次遗忘了地球的父母、同伴与爱人。此处,人与植物融合的过程被描绘为记忆与情感被阉割的过程,绿星人之间整齐划一的思想、母树洗脑式的“爱”诱导了主人公,使之自甘退化,沦为种群繁衍的工具——融合意味着人对自由意志的放弃,昭示着人与“他者”较量之中彻底失败。
《绿星居民》带有一定的反乌托邦色彩,展现出对单一意识规训个体自由的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选择“植物”而非“机械”或其他外星智能体作为意识入侵的媒介,正体现了“植物恐怖”(Plant Horror)的叙事逻辑:沉默、静止、低等的植物颠覆了进化论的理性秩序,而人本身乃至人类文明随时可能被入侵、被吞没。
融合中共振:“万物共生”的想象
然而,随着技术发展加速、全球生态危机加剧,在人类足以成为甚至乐于成为“赛博格”的今天,“后人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处境。越来越多科幻作品开始重审人类与自然、与非人生命之间的关联,探讨人类主体边界的瓦解的积极面向,科幻作家笔下的人植融合也被赋予了共感、扩展与再生的伦理潜能。
新生代科幻作家陈楸帆的《菌歌》则是具有代表性的文本之一。尽管真菌在生物学划分中不属于植物,但科幻小说中的真菌足以被视为一种“植物性存在”。小说中,工程师苏素深入篁村,意在说服村民上传村落数据,将之接入“超皮层”网络技术系统。但任务过程中,苏素与篁村所建立的情感联系,使她在祭祀中将意识接入菌丝网络,获得了联通万物的感知力。苏素意识到,真菌网络已经存在数千万年,人类与之相比宛如婴孩;她感受到“温暖而博大的震动”,“那种爱像是长出无数细小的菌丝,紧密地联结在苏素的意识之中,只要她心念一动,便能领悟到与之相连的所有生命的脉动”。
此时,人植融合不再被视为一种退化,它被描绘为对自我边界的扩张与超越,唤起的是敬畏与感动,进而导向人类对自身定位的再审视。如同作者所说:“共生是生命的真相”,远在互联网发明之前,人类便已嵌在亘古的生态之网中,而“所有的动物、草木、石头、真菌都比人类更加智慧,它们知道自己是万物的一部分,接受自己的使命,懂得何时奉献自己。”
苏素与菌丝网络的融合以歌声为媒介——这让人联想到庄子的“天籁”之喻。“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天籁”处于所有声音尚未分化之前的状态,是未曾分化、包蕴无限的全美之声。村落祭祀时歌师们传唱的歌谣、山川之间回荡的自然之声带领苏素超越了人类的感知边界,完成了从“人籁”“地籁”到“天籁”的飞跃:“肉身已经失去意义,苏素感觉自己变得无限大或者无限小,那也许是一回事。她成了“频率本身”;所有自然与人造的振动在意识与环境之间交换着信息与能量,与她的情绪共感共振。
在这一情形下,人植融合可谓是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具象演绎,也因此呈现出一种符合东方传统生态伦理的科幻美学。这为我们观察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后人类书写提供了一个切口:以《菌歌》为代表的科幻小说有意识地调动地方性知识,塑造一种独特的后人类主体想象:它不依赖于技术义体或信息算法的拼接与延展,而强调人与万物之间由内而外、本性具足的联系。其中,植物与人类的关系得以重建,植物从“他者”向人类的“亲属”位置回归。
融合与未来:“他中见我”的旨归
可见,在当代科幻小说中,人与植物融合,不仅是人类身体或精神层面的变异,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的一种根本性翻转。“融合”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与改造,而是走向一种结构性的“再生”。在这一过程中,植物不再只是象征或背景,而成为新的意义生产者、认知引导者与规则制定者——人类与植物成为互为身体、互为语言、彼此敞开的共生体。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是否意味着放弃人类的主体价值?
实则不然。植物的哲学意义恰恰在于给人类提供一个“他中见我”的参照维度。它们不强调控制,不追求中心,也不执着于边界,而是以根茎式、多点位、去中心的方式栖居于世界之中。这种非主导性、非线性、非个体化的存在逻辑,为人类重新思考“主体”与“共生”提供了哲学上的路径。植物所体现出的生命逻辑,不是对人类理性的否定,而是反观人类自身结构、感知方式与文明认知的一面镜子。
在这个意义上,探讨人与植物关系的科幻小说,正可以成为重构人类身体边界与文化边界的实验场。尽管在当下中国科幻小说中,聚焦于这一议题的作品仍在少数,但它所开启的思想空间极具潜力,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出现更多相关创作。
在生态文学中,我们已经追问过太多次“人类如何保护植物、保护自然”,而植物哲学则提醒我们换一个问法:“人类还能如何重新理解植物并嵌入自然?”因此,突显植物生命形态特殊性、强调植物主体性的叙事,为科幻文学打开新的可能性:它不满足于方志式的知识展览,也不囿于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呼告,而是推想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一个超越人类中心、万物和鸣共栖的世界。当然,这种认知和理念作为一个文学热题,它需要不断发生并不断开掘的具体生活。
 叶李
叶李
 王之远
王之远
(叶李,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省作协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签约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之远,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毕业生,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