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作家穆萨
青年作家穆萨
穆萨是湖北文坛近年涌现的一位前途可期的青年作家,已经陆续发表了《去海边》《猎人之死》《荒野》《冬眠》《蜉蝣》《人狗之间》等多部具有分量的作品。虽然他的作品尚未被广泛关注,但荒诞的小说气质使他的创作具有较高辨识度。荒诞不仅表现在作品基调上,还表现在作品所显示的拒绝解释的姿态上,荒诞也是穆萨用以抵抗现实保持文学刺痛力量的创作观念。
设置悬念与神秘书写的交响
穆萨小说中荒诞与悬念的设置是一体的,二者互相呼应,互相成全。《人狗之间》中的“我”从屠夫刀下救回一只狗,但这只狗在此后五年的时间里,曾尝试通过坠楼、逆车流、绝食等方式自杀,最后吞钉自杀而亡,自杀之谜是小说中的悬念;《冬眠》中的“冬眠症患者”,每年都会消失五个月,这五个月的秘密成为悬念,生与死的区别,人与植物的区别,在冬眠行为中被取消;《猎人之死》中猎人的死亡时间、死亡真相成为悬念,记忆与现实孰真孰假是悬念,野物、棕熊、狸猫、猎人等意象的交替出现,给小说蒙上一层神秘的氛围。
而荒诞书写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神秘、诡异氛围。《去海边》中冲动杀人的丈夫以自杀赎罪,妻子却在新闻里看到受害者没死的消息;《蛇》里放蛇吓人,再去抓蛇盈利的捕蛇人;《猎人之死》里“我”交付真心与金钱的发小,却是诈骗犯……穆萨小说在荒诞的情节中,模糊了荒诞与悲伤,真相与谎言的边界。这种叙事方式,看似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实则正是荒诞的核心,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遭遇,本就无法用逻辑解释。人类渴望因果,但世界往往不给答案,穆萨的拒绝回答,不是偷懒,而是冷酷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阅读穆萨小说时的挫败感,正是他要传达的体验:在荒诞面前,解释永远是无力的。
穆萨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处于异化状态。他们不是生活在奇幻世界里的怪人,而是被日常生活本身推向异化的人。除了叙事和人物,穆萨善于通过怪异的意象营造荒诞氛围。蛇与捕蛇人、熊与猎人等反常搭配,既是场景的构成元素,也是叙事的触发点。穆萨并没有把荒诞当作装饰性的技巧,他写得荒诞,不是为了炫耀想象力,而是作为抵抗现实的一种冷静反思。穆萨选择从日常裂缝中生长的故事,把生活本身撕开一道裂口。通过异化的处境与物象留白,他的小说营造了一种无可安放的不安感,用荒诞的写法接纳了现实生活中很多无处安放的灵魂。
以荒诞直面现实的荒凉
如果说穆萨小说中的荒诞在第一层面上表现为叙述方式上的冷峻与异化,那么在更深的层面上,它真正的力量来自与现实的对抗关系。荒诞并非孤立的美学趣味,是与现实互为镜像,它一方面来源于现实的荒凉,另一方面又用极端的方式揭示和反抗这种现实。穆萨的写作因此充满了紧张感,他的小说不满足于展示奇异,而是要在荒诞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撕扯感,从而在失衡之中凸显现实的本质。
在穆萨的小说里,现代都市文明拒绝自然、原始、本性,因此很多在现代文明中无法舒展身心的都市人,对自然有种天然的向往,甚至希望每过一段时间都能逃离都市,将自己浸润于自然里,回归原始野性的状态。《骷髅》的主人公是典型的社恐人士,无论是与骷髅同室而居同床而眠的行为,还是对现代社会拒绝姿态所显示的后现代性,都使小说充满先锋意味。此类人物还有《冬眠》里每年冬天像植物一样冬眠的花店供货商,《荒野》里在“无休止的工作之前放松身心”回归荒野的荒野探险者们。
穆萨笔下这些人物的共性在于,他们没有归属,无处安放。冒险、越界、背叛是对生活的试探,这些看似悖理的行为显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茫然与苍白,当短暂的放空与自由来临,文明、教养、忠诚都被抛诸脑后。《洄游》里重返故乡的画家,《蛇》里的捕蛇人,都是精神无处安放的流浪者。通过这些荒诞书写,穆萨揭示了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即在社会结构、生存环境和个人情感的多重挤压下,个体越来越难以找到合理的位置。
穆萨的荒诞是用断裂、异化和留白等方式,去直面现实的荒凉。在现实生活中,文学是解释生活的,在穆萨的小说里,文学是打破解释的。他让文学重新回到追问的本质,不给答案,只留下刺痛。这些方式的共同点,是坚持制造一种不适感、困惑感和刺痛感。穆萨的写作不是要回答现实问题,而是要保留现实问题的难堪。他的荒诞书写,正是抵抗现实的一种方法。如果作家只是顺从逻辑去书写,文学就会失去锋芒、失去反思现实的锐度,穆萨选择用荒诞揭开现实的裂缝,保持文学刺痛的力量。
荒诞是拒绝解释的姿态
穆萨的小说设置了很多悬念,这是造成小说充满神秘氛围和荒诞气质的主要原因。因为神秘、奇崛的想象力,小说充满了挠人心魂的悬念,但作者没有急于揭晓悬念,也没有沉浸于设置悬念,而是在舒缓的叙事中交代情节走向,结局都在淡然、舒缓的节奏中结束。无论是“出现零星灯火,小镇转瞬即逝”的结局(《荒野》),还是“他要前往城市了,可他的布袋里一条蛇也没有”的结局(《蛇》),以及“我拉上窗帘,换上刚脱下的还有余温的睡衣,不打算出门了。让植物沉睡。”的结局,都有种“其余风景,留待读者慢慢品味”的淡然潇洒。穆萨擅长在平静的叙述中埋藏情感与命运的暗流,节奏舒缓却并不拖沓,往往在细节中积蓄情绪,最终爆发或转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张力。
人们习惯用逻辑解释一切,用理性安排生活,用叙事安放命运。文学一旦顺从这种惯性,就会沦为现实的附庸。穆萨的荒诞写作,正是对这种惯性的撕裂,这种撕裂,构成了文学的刀刃。所以,在穆萨的小说里,人物往往被推到存在的边缘,这些极限经验,在现实叙事中往往被规训,被安置在社会或心理的框架中。但穆萨用荒诞的方式,把这些经验从常规的解释里解放出来,让它们呈现为无法解释的裸露状态,把人类最根本的孤独、恐惧、迷失,呈现为不可调和的存在。这种极限表达,不是心理学的,不是社会学的,而是文学的,只有文学,才能通过荒诞来书写这些无法言说的经验。
现在的青年写作普遍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现实的表层模仿,写日常琐事、写青春困惑,但缺乏更深的力量;另一种是对想象力的单纯追逐,把小说写成玄幻或类型娱乐。前者太浅,后者太轻,穆萨的荒诞写作显然不属于这两类。他既不是琐事的复写,也不是幻想的逃避,而是以荒诞作为文学的锋刃,直面现实的困境。走出自己的经验,走出故乡的经验,选择从有难度的创作姿态开始,这对青年作家来说需要勇气,穆萨进而表现出成熟稳健地把控故事的能力、冷静克制但又富有沉思性的语言风格、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思考,都证明了他在创作上的巨大潜力。但穆萨的小说也存在很多青年写作的共性问题,如缺乏历史感知、知识沉淀、经验积累等,忽视了与现实、历史、经验的衔接,这种技巧若把握不好,就容易滑向生硬,显得像是为了荒诞而荒诞。他的小说篇幅还有扩展的空间,结构还欠缺张力,有时像是一种想法的速写,而不是经过充分生长的有机体。
对于青年作家而言,或许写作技艺上的任何不足都不致命。真正的问题是,要警惕固化的荒诞书写,要敢于突破自我,探索更多创作的可能性。一旦荒诞变成自我重复,失去与现实的内在摩擦,创作就会失去深度,变成一种装饰性的技巧。青年写作不缺想象力,也不缺技巧,而是经历和经验的沉淀。穆萨的小说可以在荒诞与现实之间建立更深的联系,也需要让语言与形式探索真正内化为小说深刻思想的载体。如此,荒诞书写才不会演变成自我复制,反而会成为创作持续的发力点。
 本文作者汪亚琴
本文作者汪亚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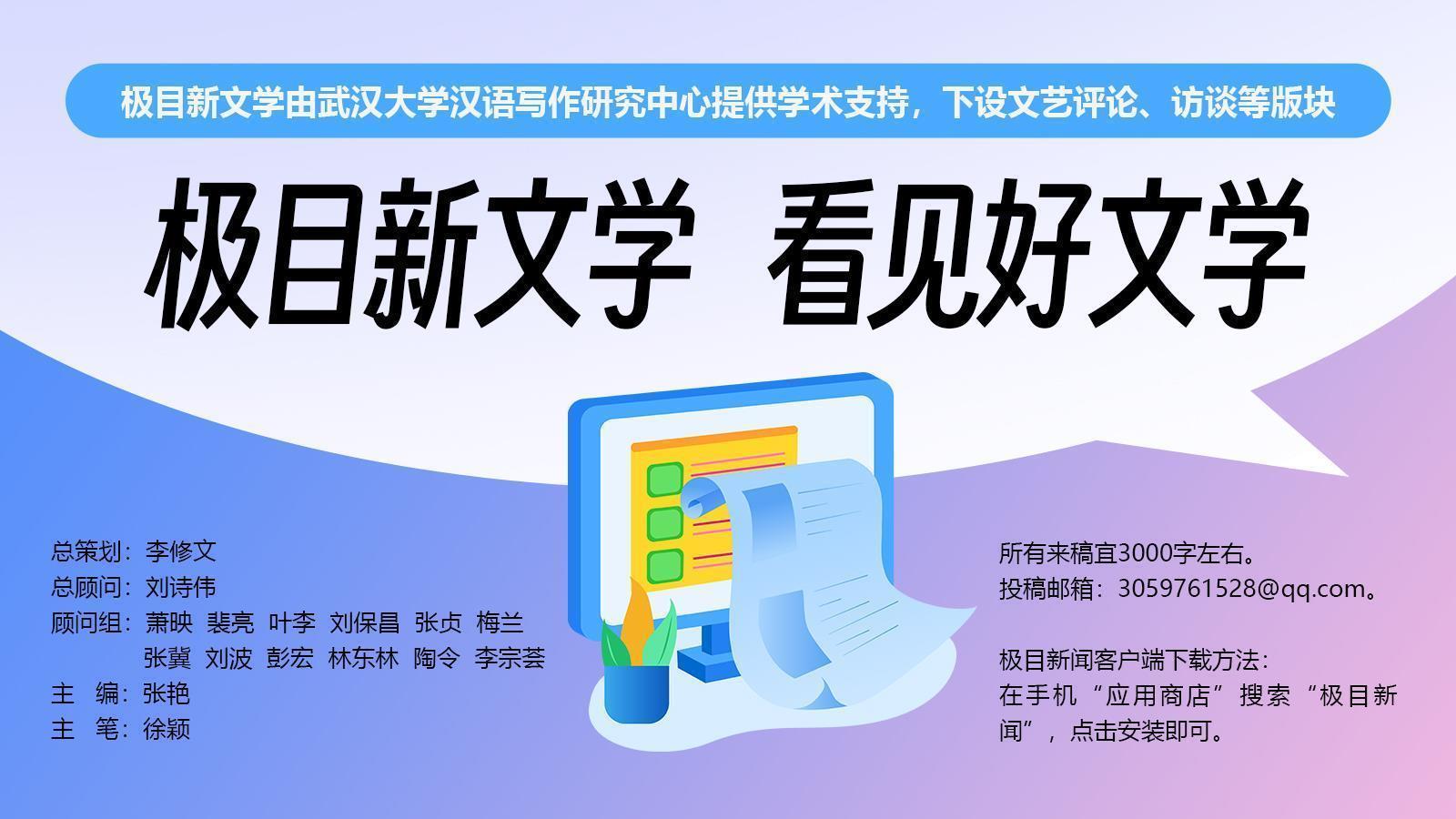
(汪亚琴,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协第三届签约评论家,2025年度“湖北新时代文学研究”支持计划“湖北青年作家创作中的荆楚文脉传承与重塑研究”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