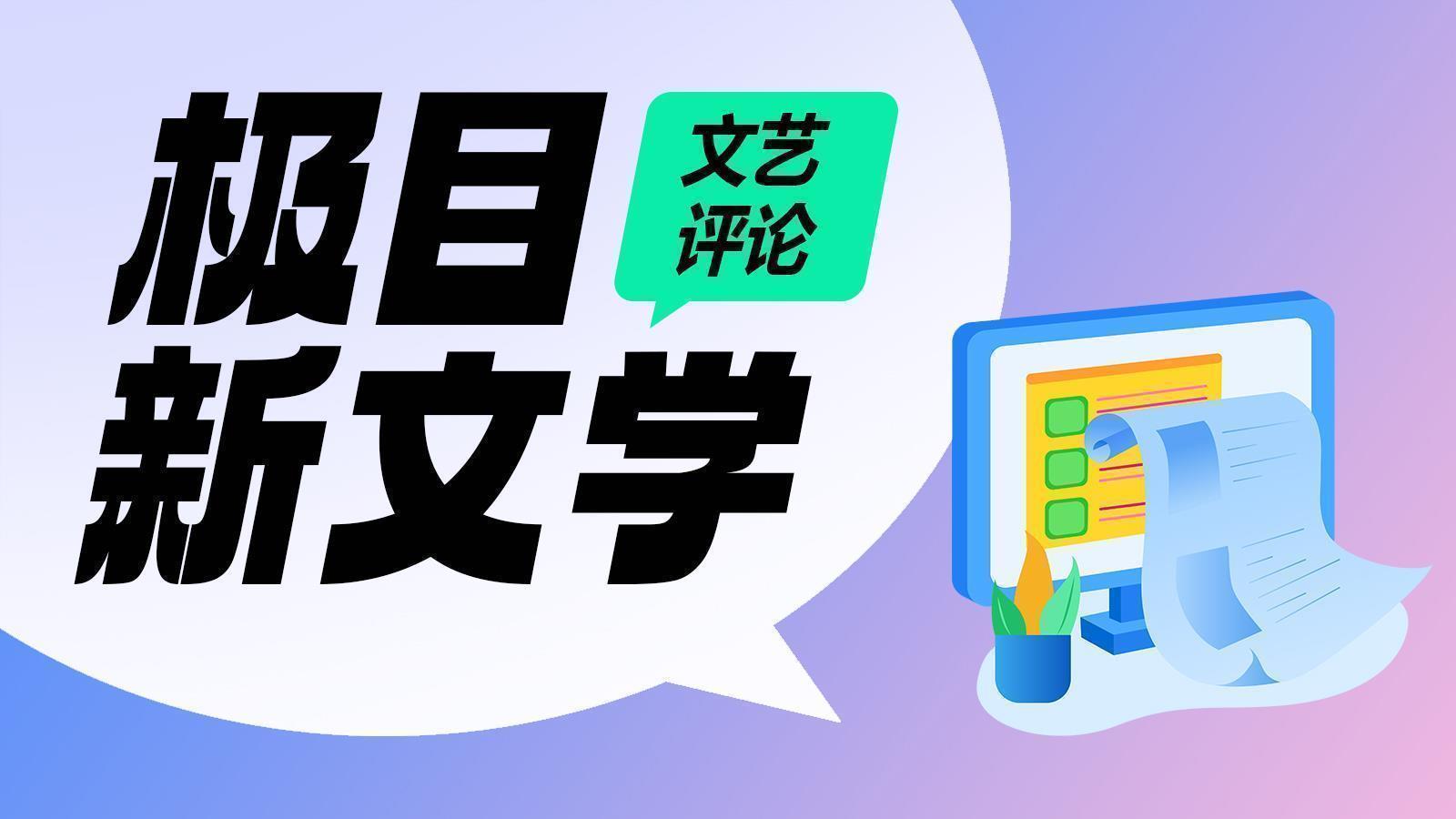
《何不顺流而下》是武汉作家喻之之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小说发表在《长江文艺》2021年第一期,同年被《小说选刊》第三期全文转载,后收录于小说集《四月的牙齿》(花城出版社2025年版),并位列首篇。
小说以散淡笔触形象地书写了艺术家老K在体制、爱情与艺术追求之间的挣扎与突围。尽管这一题材在现代文学中已然成为一种叙事母题,但喻之之的独特之处在于并不是简单地编织一个“艺术家逃离世俗”的故事,而是通过故事深刻表现现代人的某种生存境况与精神突围。
存在的困境:马与楼梯的隐喻
小说开篇写道:“老K很想养一匹马”,然而他住在闹市公寓三楼的两居室,“马没法上楼梯。你知道的,会劈腿”。“想养一匹马”,这是老K真实的愿望,但这一想法对于住在公寓里的老K而言也是荒诞的,由此隐喻现代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马在文本中是一个意蕴丰富的象征符号,代表着自由、野性、自然与未被规训的生命力。老K是“城市有名的才子”,熟读四书五经,擅画花鸟人物,梦想在大街或者大道上“骑着一匹意气风发的枣红马穿街过市”,“把马系在院子中央的那棵海棠树下”。这一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画面暗示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楼梯则象征现代社会的规则与制度。马无法上楼梯并不是因为它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为楼梯设计之初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马的特性。在社会里,所谓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就是个体的天性、才华与梦想往往难以适应标准化的规制结构。
老K放弃养马的真正原因是他想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汽车会越来越多,马会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他想象到马系在海棠树下委屈的模样:“它甩动着尾巴,低垂着头,打着响鼻,大眼睛眨巴眨巴的,感到很委屈。”这一令人心痛的场景,形象地揭示了一个敏感灵魂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那些不适应规则的生命,即使勉强存在,也只能在夹缝中委屈生存。
通过“马与楼梯”的隐喻,作者提出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命题:在不适合本真存在的环境中,个体该如何自处?是强迫自我改变以适应环境,还是积极寻找或创造适合自己的空间?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这组彼此相对的问题贯穿全文,成为老K后续所有选择的基本背景。
老K所在的文化单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机构。小说对这一空间的描绘是,“一眼望去,它就在告诉你,我很风雅,我很风雅。文化单位嘛。”表面的“风雅”掩盖不了内在的具体情形。老K在单位中的处境非常尴尬:“像是半边身子在门内,半边身子在门外”。体制需要他的才华(如为领导女儿考学作画),却不需要他的独特性;承认他的价值,却不愿给予相应的尊重。
账本事件集中体现了这种异化关系。老K莫名其妙地收到一本空白的账簿,随后他被怀疑包庇会计老葛而遭受调查。这一情节具有卡夫卡式的荒诞色彩:空无的能指(空白账本)成了权力运作的借口,个体陷入自证清白的无限循环。
老K的辞职宣言在朋友们的演绎中被戏剧化为“老子不干了!本老爷不屑与你们为伍”的慷慨陈词,而实际上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不干了”。这一反差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理想主义行为本身的软弱性。当然,也可以说理想它不需要戏剧化的装饰和表演,只需一个清醒的决定。
从“养马”理想的破灭到最终“我不干了”的清醒决断,老K完成了一次对系统性压抑的突围,象征性地回答了开篇提出的存在性命题:当环境与本性相悖时,个体不应被动地忍受扭曲,而应主动“顺流而下”,去寻找或开创一片能让生命得以舒展的“天兴洲”。
爱情的悖论:小布丁作为未完成的救赎
老K与小布丁的关系构成了与“环境困境”并行的“情感困境”。小布丁是现代社会精神症候的缩影。她既吟诵着“回到母亲子宫”的诗句,渴望田园牧歌式的绝对安全与简单生活,又被牢牢锚定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之中。更为复杂的是,她的情感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她似乎依赖老K的照顾,却又通过坚守前男友的咖啡馆,活在对过往关系的想象性维系中,这使老K的爱情始终蒙上了一层“替代品”的阴影。
小布丁的抑郁症超越了单纯的临床诊断,成为存在论隐喻。代表着高度物质化社会中普遍的精神“失根”状态。她将雨天行驶的车内比作“母亲的子宫”,准确传达了她对免除一切社会性责任的婴儿式渴望。老K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个“子宫”的角色,提供无条件包容、安抚与物质满足的庇护所。然而,这个庇护是单向的,老K在持续付出中消耗能量,却难以获得对等的情感滋养。这不是两个独立个体间的平等对话,而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共生。
怀孕事件成为打破这种停滞状态的转折点。对小布丁而言,怀孕是将悬浮关系“实体化”的努力,是通过爱情结晶构筑稳固“小家”的尝试。但对老K,这声“我怀孕了”不啻晴天惊雷。这意味着残存的自由将被收缴,尚未厘清的人生将被更沉重的责任固化。他的沉默与离开,并非简单的懦弱,而是清醒灵魂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本能退缩:一个连自己的“马”都无处安置的流浪者,如何承担引领新生命的重任?
老K的逃离不能简单解读为对爱情的背叛,而是对以“爱”为名的新型束缚的识别与拒绝。老K的出走,是他捍卫个人精神领地完整性的延续。在他自己尚且步履蹒跚、需要寻找一方能让灵魂栖息的沃土之时,无法成为他人的救世主。离开小布丁是从注定失败的“救赎幻想”中清醒,为他最终“顺流而下”、寻找天兴洲这一真正归宿扫清最后的障碍。
艺术的出路:从单位附庸到本真创造
老K的艺术生命轨迹,勾勒出一条从规制化生存走向本真性创造的精神路径。
辞职后的困顿期是老K艺术生命必经的“阵痛”。脱离单位,直面市场残酷与生存压力,促使他的艺术发生根本转变。他不再画那些迎合预期的行画,而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他画孟浩然在襄阳,李白在钟南山,孟浩然锄豆,李白醉酒,王摩诘在辋川别墅晒肚皮……有的没的,他都画,画了别人没画过的题材,画出了别人画不出的味道。”这标志着老K艺术完成了从外向内的根本转向:他从迎合外部标准到表达内心真实,从复制范式到自由创造。
画作《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创作与封笔是有深意的艺术事件。广州老板以重金收藏并约定“以后再不许画这个题材”,表面上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实则揭示了本真艺术的特征:真正的创造是不可重复的,它是特定生命状态下灵魂的直接流露。这种“一次性”恰恰是对艺术商品化、批量生产的最大反抗。老K遵守约定,转向其他题材的创作,证明他的艺术已摆脱对特定成功模式的依赖,进入创造的化境。
天兴洲的选择则是老K艺术的终极实践。这个位于“武汉的下游”的沙洲,是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没有电力,“完全靠太阳光过活”。在这里,时间回到了最自然的节奏,生活与创作重新合一。他养马、种西瓜、画画,构建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这种选择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另一种存在方式的积极开创。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洲上依然创作,但“不急着卖”,艺术重新回到了它最初的意义。
“何不顺流而下”的标题在此获得了完整的哲学意蕴。顺流而下,不是随波逐流的消极,而是顺应本心、寻找自身生命河道的智慧。老K没有选择一般推崇的“逆流而上”的奋斗哲学,而是选择了看似退却、实则更加积极的“顺流而下”。这种选择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避世”“隐逸”的精神资源一脉相承,但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它不是简单退隐,而是在认清现代社会的异化本质后,理性选择的本真生存方式。
小说主题思想同样源于叙事艺术上的成功探索。喻之之通过意象系统的精心营造,构建了一个丰富的象征世界。从开篇的“马”到结尾的“西瓜”,从“账本”到“脐环”,每个意象都承载着多重的象征意义。特别是“雨”的意象,它既是小布丁抑郁情绪的外化,又是净化与再生的象征,还是老K观察院子、激发艺术灵感的媒介。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则既保持了与主人公的心理距离,又通过“我们”的视角提供了必要的补充与反讽。而对李白、孟浩然、王维等唐代诗人的当代重访,不仅延续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更通过“孟浩然是吃蝙蝠死的”这样的荒诞考证,完成了对学术体制和理想化解读的解构,为老K的选择提供了更深厚的文化语境。
 本文作者陈国和
本文作者陈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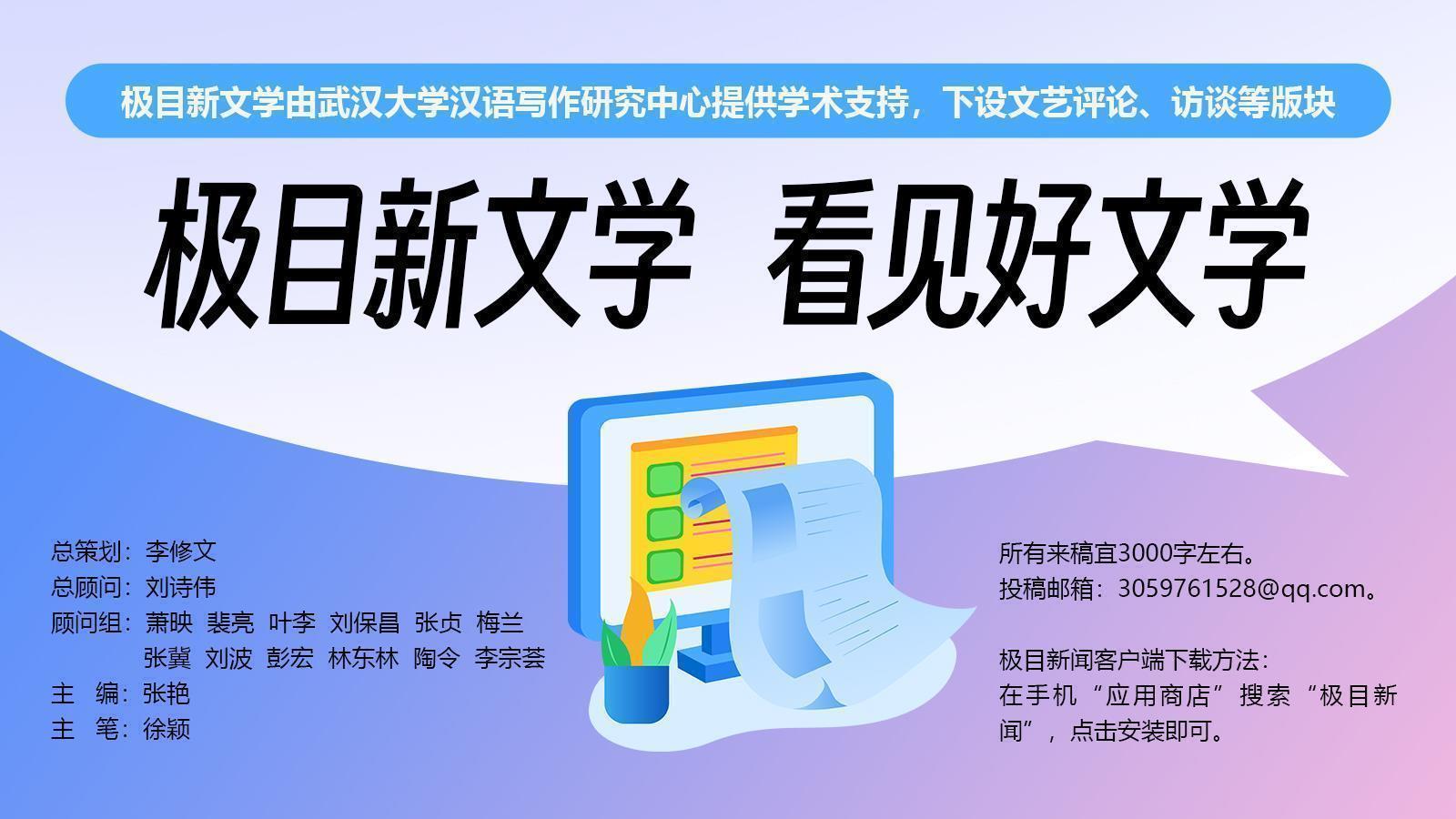
(陈国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