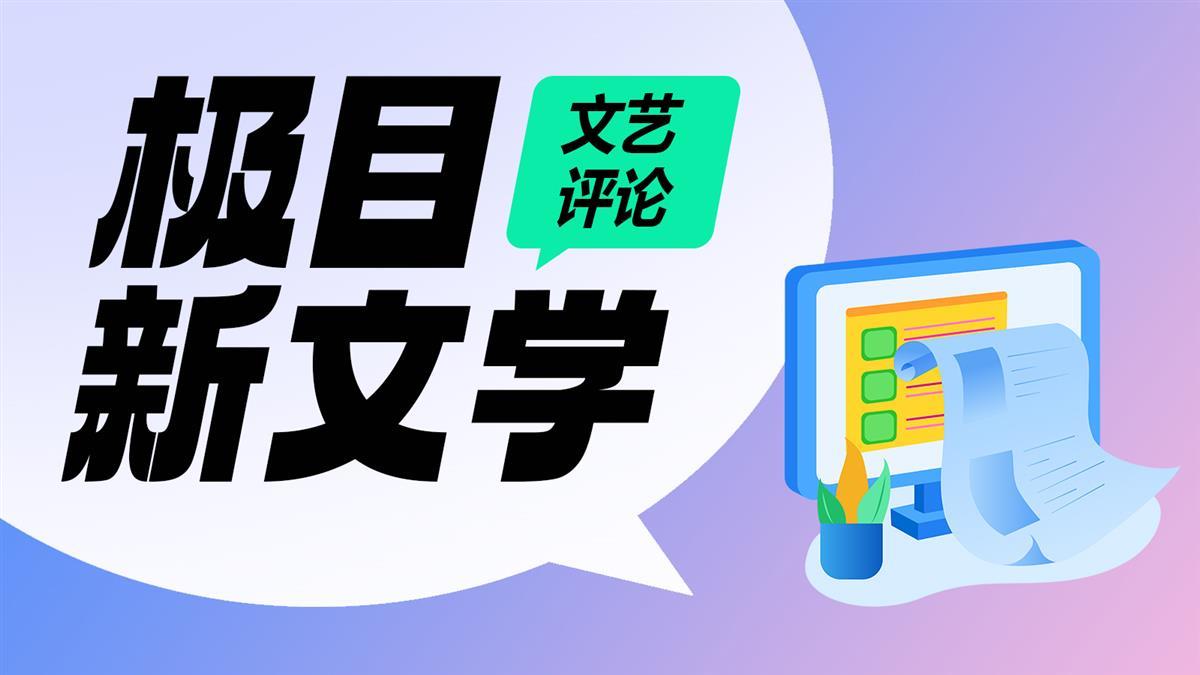
诚如叶立文教授所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文学的危机似乎从未像今天这般令人忧思。”由此,我联想到文学史上因时代进步引发的文学变革:如中国“两汉”时期的文学体裁之变,孕育和产生了汉赋、五言诗、叙事散文等文学样式;如欧洲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了与时代精神契合的人文主义文学;又如当代传播语境中出现的文学影视化现象。
但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之变与任何时代的文学变革都不一样,这一次是AI直接披挂上阵从事文学创作了,这是创作主体之变,颠覆之变。
现在的问题是:AI能否替代作家的创作?作家能否干过AI的创作?
作为一个文学人,我个人的认知是:目前AI的所谓创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因作家基于个体感知、个体经验、个人美学而独创的具有本质新意的艺术世界和思想意蕴性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
关于人工智能(AI)现在的创作和未来创作的可能性,目前坊间存在多种说法和观点,有人认为它可以赋予文学创作更多新的形式与可能,有人觉得它难以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也有人对它的未来寄予期望。
为及时回应这一问题并进一步探讨,特邀几位当下活跃在文坛的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一起参与讨论,他们各有精彩表述,我从中得到的一个“公约”立论是:独特的个人美学,才是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创作的生存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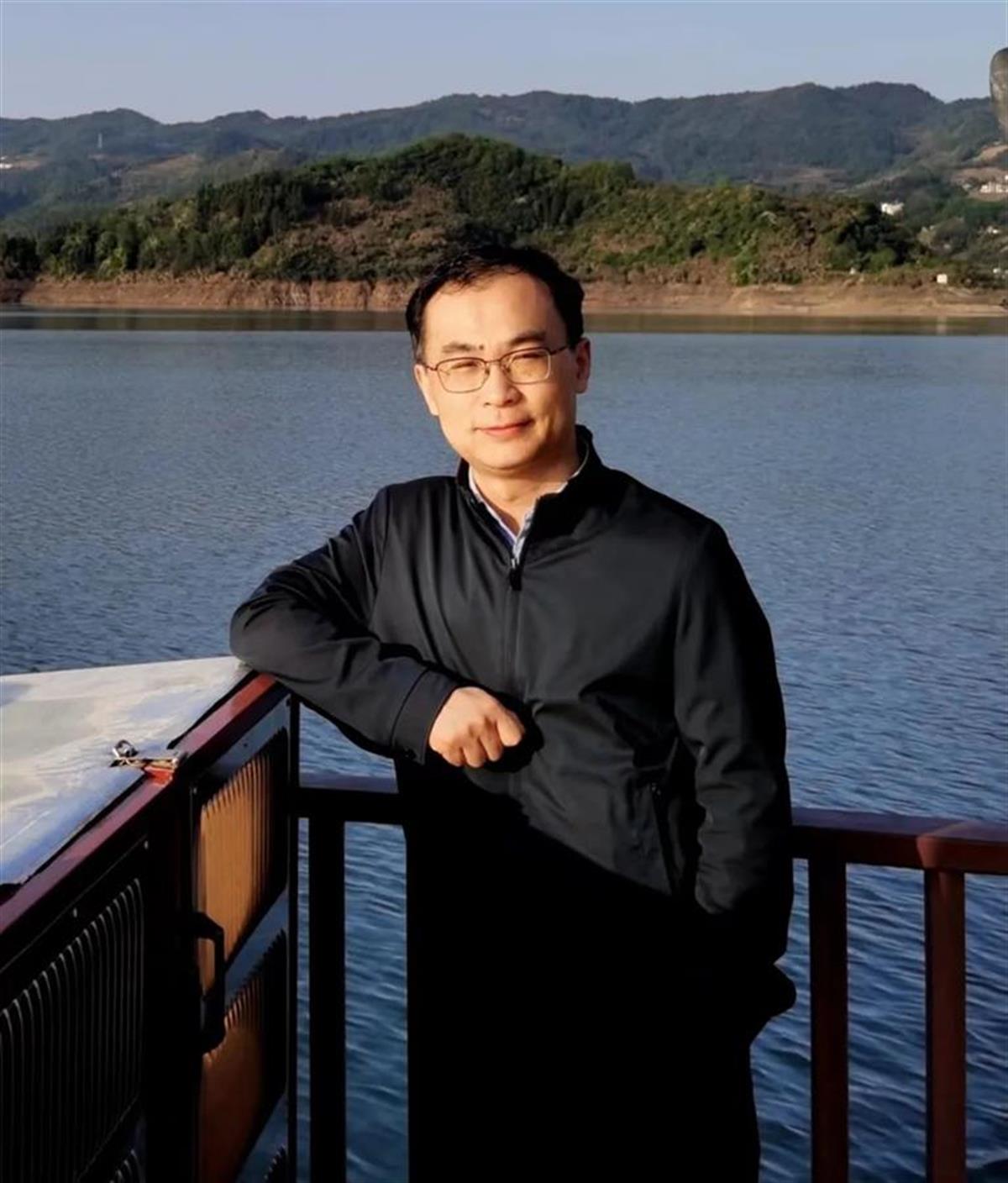
蔡家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主编,评论家、作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创作出了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诗歌、散文和网络文学,惹得很多写作者惊呼“狼来了”。但细细分辨,从这些作品中还是能嗅出一股“机器味儿”——程序性写作的痕迹。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无论是ChatGPT,还是Deepseek、豆包等,都是通过大语言模型建构起来的,并且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而获得优化。它们获取的信息量越大,其智能表现就越佳。面对庞大的数据库,AI处理信息时会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譬如多数据优先选择、权威工具书优先选择,等等,这说明它对信息的理解是概率性的,生成的信息自然也是。就本质而言,AI写作是一种“概率游戏”,它创作的作品,其布局谋篇或遣词造句方式都是概率性选择。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发乎情”的主体实践,与感性体验和生命冲动息息相关,而创作主体对存在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AI遵循算法原则,在处理差异化的感受和情感方面显然毫无优势。这就意味着,套路化的、平庸的写作很容易被AI取代,而真正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文学创作,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对其构成威胁。当然,未来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当人们越来越有效地运用更加高级的ChatGPT、Deepseek等工具时,会发明出一种人与机器合作的新文学——人工智能文学。人的深度参与将使得这样的文学不再只依赖数字模型,而是带有生命特征,具有美学上的创造性。

张执浩(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文联文学院院长,诗人):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套用一句流行语:未来已来。那就来吧。对于AI写作,我们目前所持有的观念仍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里,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尽头在哪里。就目前的情势来看,文学创作乃至整个艺术门类的创作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且随着海量数据的不断涌入、语言大模型的加速迭代更新,这种局面也将超出我们碳基生命的把控能力。但我依然相信,文学创作这种精神活动不可能完全被硅基生命体所取代,因为,不是文学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文学,而这样的需要最终会确保文学的终极意义不会就此丧失,即,我们终将从写作这一行为本身获取自救的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学从来不是逞强斗狠,不是日趋正确或真理在握,恰恰相反,文学呈示的是人类自身的渺小、脆弱和不堪,是一种示弱的勇气。
作为置身于这一时代的诗歌写作者,我们也应该警醒地看到,那种缺乏个体生命体验、只擅长在修辞领域打转、没有独特的个人美学的作品,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诗歌终究是一种声音,它不是简单的发生学,而是更为高级的发声学,你的语调、音色和气息是AI创作无法复制的(至少目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应当在发声学的层面上展示自己独特的语言驾驭能力,勇于败笔求生,把写作本身视为生活对自己的额外奖赏。

叶立文(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文学的危机似乎从未像今天这般令人忧思:AI强大的写作能力和看不到尽头的发展前景,会不会让文学的消亡成为现实?而每一位以文学为志业的人在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冲击时,是不是必须改变自我,争取成为那个无法被AI替代的写作者?对此,我的看法是文学不会消亡,而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与生俱来,再令人炫目的AI写作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的情感与经验。
面对AI的挑战,每一位写作者只要忠于自我,不轻易被流俗的公共经验所裹挟,那么文学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终将在AI的技术进化中得以保全。我之所以有这一判断,是因为AI写作从根本上看仍是技术复制时代的产物:不论是ChatGPT还是Deep seek,都依赖庞大的资料库而存在,那些被数据化了的作家作品,构成了AI写作的“前文本”。由此也就意味着AI还不会创造文学,它只是海量数据的搬运工和加工者,而矫饰这一切的武器则是语言的花腔。换句话说,要想应对AI写作带来的挑战,作家就必须尽力避免文学的同质化。尽管文学传统无处不在,但“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汝之蜜糖,彼之砒霜,一味浸淫于文学传统的结果只会剩下“影响的焦虑”。鉴于此,作家更该有理由忠实于自我对世界的感知和看法,因为只有艺术个性,才不会让写作者堕入AI编制的技术神话。

舒辉波(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文联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目前尚无法判断人工智能是否是人类的最后一次科技革命,但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通用性和赋能性,能深入到各个领域并带来深刻变革,正在呈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多意想不到的变革,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经济结构和文化形态。人工智能可以处理和分析海量的数据,发现人类难以察觉的模式和规律,帮助人类突破自身认知局限。这种对人类认知和能力的极大拓展,有可能是科技发展的一个巅峰阶段。
但目前看来,对于文学创作,人工智能仍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不能成为创作的主体。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在对既有文学样本海量学习的基础上生成的“创作”,这样的创作注定它是“二手”的,而真正严肃的纯文学推崇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个性化的陌生表达,是目前的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据说付费的人工智能可以创作出所谓的“风格化”文学作品,但那也只是对“风格化”的一种模仿,而不是创造。就我个人的经验,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是有着自己的局限和神经的,无论是它提供的“创意”,还是它选择的“语言表达”,都太“套路”,太“网络文学”而显得偏“通俗”,与我个人的文学审美和趣味相去甚远。

穆萨(青年作家,在读文学博士):
作家肖洛霍夫在1925年所写的一部短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幕:老人阿尔焦姆站在田边,指着正在耕地的拖拉机说:“整整五十年我靠牛干活,牛靠我过活……如今有了这玩意儿,叫我怎么受得了?”随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一个漫长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时间过去一百年,没有人再为人畜农耕的结束而惋惜,如今相似的危机感则又出现于大量正在被AI介入的行业中。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时期,技术性失业不可阻挡。精神劳动同样无法幸免。因此,仅有功能性而无创造力的写作已被大规模取代。但真正有个性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正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着AI的参与。芥川奖得主九段理江直言自己的作品有5%直接取自AI的生成。这也证明了以AI作为辅助方式参与创作的行为不可阻挡。当然,我以为这并不会损害作品本身的价值。深究起来,写作从来都不是一种完全由作者独创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AI是作者的朋友而非敌人。
既然技术的变化必然导致作品生成方式的变化,作者和读者对此只有接受而已。而作为小说写作者,比身份危机更值得思考的应当是如何用作品应对时代剧变,如何去反思和书写变革前后的世界,我想这既是文学本身的价值所在,也是AI时代下作者的生存之道。
(丁东亚,青年作家,文学编辑,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
 丁东亚
丁东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