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好多好多年没想动笔写点什么了。
不可否认自己的懒惰战胜了那一瞬而过的种种感悟。
对随着年龄越来越迟钝的感悟,也是那样不想用长篇幅来言说。
记得刚刚结婚那年,我流水一般记录了婆婆家所在小村过年的种种风俗,后来的这些年,每年凭毅力抵抗着寒冷,抵抗着生活条件的贫困,抵抗着思念自己家人,抵抗着每逢过年都会有的落寞,再也没有记录过了。
今年,在这个年已经过去的今天,我却格外想回忆一下这个小村,尽管它对于我而言已不再新奇。
每年到老家的36小时之内,都要回答至少三十遍“什么时候回来的”,
尽管我们从村口开车一直到几乎在村尾的婆婆家一路上已被几十双眼睛看到,
而谁谁家儿子带媳妇回来了的消息也会最多在半小时之内传到全村所有人的耳朵。
我曾经认为这是人的朴实,后来认为这是人的虚伪,现在想想,朴实虚伪有何妨?无非是一种客套,寒暄。总之本质是善意、热情而热烈的。

图解1:腊月二十九,乡亲开始敲锣打鼓。不知是对在外游子回村的一种迎接,还是对即将到来的又一年的庆祝

图解2:村里人以“红色”为最喜庆的颜色。
每每到家的第二天就是三十了。
三十这天并没有东北的热闹和欢天喜地,
被用棉花杆点“灶坑”散出的浓烟熏醒的清晨,
屋内屋外一样温度的彻骨的寒冷不会因为这一天的不同而例外,
起床到穿好衣服的五分钟即便是文字上也是不敢面对和回味的。
起床之后百无聊赖,胡乱塞一口永远不会喝惯带着菜汤的玉米面粥,或者干脆不吃,然后就会让先生带着呵呵去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田地里打发时间。
或是去镇里赶集,或是在雪地里跑跑跳跳,偶尔仰一捧雪,心里也会被脚下这几千年大地的质朴打动。
我天性嘻哈,并没因为每年增长一岁改变,
先生脱离了工作,也似乎少了一种性质的压力,
总之,那几小时总是轻松快乐的。

图解3:镇里的大集,卖各种年货。真的很挤,真的很吵,但真的很热闹,年味儿十足。
中午回到婆婆家,依然是不透亮的小屋,依然是浓烟滚滚的空气,却要开始包够四五口人几天吃的饺子。
看着那如山的饺子馅儿,看着那一大团面,虽然手冻的伸不出也要无聊的参与。
婆婆和妯娌会用家乡话聊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我基本不语,只用心对抗着一坨一坨的面,而并不期盼此番成果有多美味煮熟吃下。
对于我而言,那是没有结果只因为“应该”而要做、而去做的事情。
好在,几小时过去,几百只饺子包完了,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全然不知道,
或许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跟院子里终日不断的不知是谁家的孩子聊几句,
或许赶快到奶奶屋里用热宝暖暖冻成冰的双脚,
或许更多的是就着一点微光读读书,哪怕暂时熬过几分钟也好。

图解4:先生的侄女,11岁,喜欢参与奶奶、大伯母和妈妈的饺子行动。
大年三十的晚上注定是要只吃饺子的(只吃!除了饺子什么都没有),
我于是会怀念未出嫁时从三十到十五爸爸做的12或16个菜,那时候从早餐开始就要摆一大桌,
中午晚上,爸爸会问我,爸做的锅包肉不好吃吗?好吃啊。好吃你怎么不吃啊?我肚子满满的,哪儿吃的下啊。那你吃个螃蟹吧,当零食吃,加起来也没一口肉。
遐想完毕,我还是舍不得外面轰隆隆的鞭炮声营造的过年的气氛,横下一条心把碗里的第四只或第五只饺子吃完。
婆婆通常不让我收拾碗筷,我会抢,其实真的是想由我透彻地里里外外刷刷那些碗筷的。
收拾完碗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盘到奶奶炕上了。
因为煮饺子而烧的炕头好热乎,虽然屋里的光是看不了书的,可只要暖,就足够。
春节晚会通常看到九点多就睡着了,手机在手里也是响个不停,我却常年只收不发。
再醒来,就是大年初一了。

图解5:侄女,依然是孩子心性,除夕夜,拉着我去放孔明灯。
大年初一,往往会被人声吵杂惊醒。好黑的天,打开手机,刚过五点。
隔壁厨房婆婆掀锅盖的声音伴随着婆婆叫起床的声音有点吵人,
五点多屋里和外面一个温度真的很冷,所以我每个大年初一都伴着无法摆脱的厌世情绪骂无数遍变态风俗翻无数个跟头后咬牙起床,
起床后照例只吃饺子,我照例只吃五个以下以维持生命。
六点钟吧,或许早餐的饭桌还未撤下,就有一大家一大家来拜年了。
一家子的男人和女人总是分开的,男人拜年通常较早,有一来十几口的,也有几口甚至一个人的,进门就跪在祖相前,参差不齐喊着过年好。
我们那九十余岁的奶奶,也总是踮着小脚边扶边嗔怪着大家为什么要跪,枯瘦的手里抓着冒了手缝的糖或瓜子往同来的孩子们的兜里揣。
有的人会到奶奶房间坐上十几秒,寒暄问“奶奶挺好的”之类的话,仿佛他们和奶奶并不是天天见面而是几年才见一次,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家庭人口多的人就不进卧室,直接告别前往下一家。
陆陆续续这样到八九点,就是女人们来拜年,院子里、屋子里照例杂乱起来,说笑声、呼喊声不绝于耳,也无法辨认她们在说些什么,无法确知她们快乐在何处、为何哈哈大笑。
(写到这里,想起高洋童鞋曾经说,女子无才便是福。或许吧,快乐的那样纯粹、简单。)
所有拜年的人中,还有一位老人让我印象颇深,他大概六七十岁,是自己来的,我没有询问我先生他是否无儿孙。他的腰已经弯的快90度了,走路也一颠一颠,他进屋要跪,奶奶说什么也没让,强拉着起来,两位老人说了会儿话。奶奶说,这老头的老伴自从嫁来后,这些年从来没给别人拜年过(想来或许是如我一样叛逆之辈,哈哈,不过俺可是知道入乡随俗的道理的,心里虽然骂着可表面上还是能做到位的)。我送他出大门后,一方面感动于奶奶的好人缘,奶奶是全村年岁最长的老人,她和已故的爷爷一辈子都乐善好施,赢得了全村人的爱戴。另一方面也感动于村里人这种对长辈表示尊敬的方式,像这位老人,他住在村子最东头,奶奶住在最西头,他身体那样还坚持在这一天来看望奶奶,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
我猜,在全村人的骨子里,都和先生一样,从小就认为初一上午的拜年是中神圣的仪式,是不管在外面见过多少世面混得有多好,回家都必须履行的。

图解6:每年除夕上午要悬挂在中厅的大幅,上面画着祖宗的排位,写着祖宗的名字。旁边的黄纸撑起来放在大幅前面的贡品桌。初一上午,村里人挨家挨户会来跪拜,以示对先祖的敬意。中间的白色纸是初二交到族里,统一在村口烧掉的。上面写着户主的名字,某某某带领全家人在……神位下……
每年初一上午,我都盼着先生的回来。
现在他只能跟弟弟一起去拜年了,我很怕哪年弟弟因为工作,过年无法回老家,只先生一个人到处拜年的情形,他该是多么落寞孤单。
我生性喜淡,平生最最最恨吵杂热闹,盼他回来,多半也只是希望自己这种硬着头皮的坚持有人理解、或者说给自己一个坚持的理由。尽管他根本不会理解。
初二的早晨可算睡了个懒觉,八点多时先生趴在我耳边说,快起来吧,今天送泰山奶奶,都在村口放炮,村里人会说送的是“爷爷娘娘(音译)”。我因为有初一一天的铺垫,对村子里我从没感受过的风俗也产生了好奇,于是嚷着要去看。我也曾经跟先生笑言爷爷和娘娘又不是一辈份,又不是夫妻,如何能搭配?仗着不知者不怪冒犯了仙人;也有说法说是送“泰山奶奶”。不管是爷、奶、还是娘,总之是送一位掌握大权的仙人,确保TA能在路过村口满意了这种招待而略施恩惠保全村平安、风调雨顺、收成好等等。
先生说,村子里虽然绝大多都是姚姓,但从宗支来讲,分为三支(不太懂,可能是好多辈好多辈之前,村里只有三个姓姚的老人,他们就是三个“支”吧)。每年三十之前,由每支负责的人拟定当年烧纸放炮的数量和金额,然后宗支人均摊费用,统一买了纸和炮后,再分给各户,先生所在家族是人数最多的一支。初二,由张罗每家收纸钱的人安排人抬着巨大的簸箕,里面装着初一晚上各家各户收的纸钱、写满字的纸屋子等等去村口,到了村口,男人们不规则但自觉的跪成几排或十几排,领头的人放鞭,烧纸。那阵势可谓浩浩荡荡。三个支的男性都去村口放炮烧纸。而且互相攀比哪一支放的炮更响。
我们出去的时候,前两支姚性的已经送完了,我和先生走到村头,刚好赶上他们这支放炮。送泰山奶奶的全是男性,烧纸、跪拜、磕头放炮者显得都虔诚而兴奋。基本一挂鞭放完,另一挂紧接而上。整个仪式大约持续十五分钟。我因为好奇,也不跪,只站在队伍身后看热闹,任凭呵呵乱跑,我也全然不敢因为追它而接受这么多各年龄段人的跪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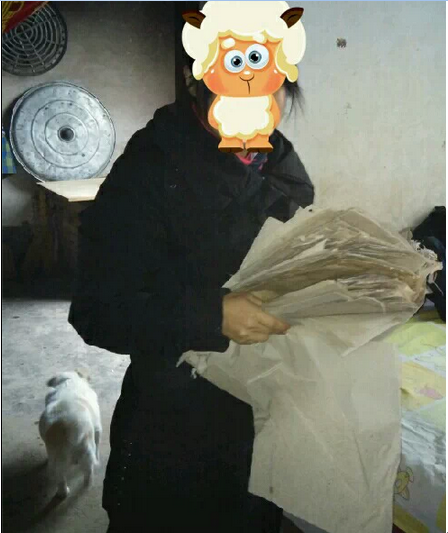
图解7.我抱着好多初二要在村口烧给泰山奶奶的纸。
这么多年,除了几个经常走动的邻居,我一直辨认不清其余人的辈分。
白发苍苍的奶奶,却要叫做嫂子;比我还年少的少年,却是爷爷辈分。
我不仅来自外乡,骨子里更有对所有事情的不羁,所以从不叫,只报以笑容、重复无数遍的客套话、或装作听不懂她们的家乡话(我的方言理解能力很强,其实90%还是会懂得)。
我很感叹她们的热情,生活在这样无趣的小村,终日过着这样单调的生活;我又很憎恨她们的八卦,因为无趣所以要找一点乐趣,找来找去,就变成了背后的戳戳点点,这也是我眼中她们生命的悲剧。

图解8:村里人坐在一起唠家常
说起家里的人,我最佩服的就是婆婆了。
她在我心里总是可怜的,尽管她也没有认为自己可怜。
她偶尔会跟我感叹她的不易,或者奶婆婆这么多年对她的种种态度,但言谈间真的没有一丝丝的抱怨,
我想,她的诉说,只是作为一代代婆媳关系到她和我这时候戛然而止的感慨(尽管她从未因为不仅不能欺负我数落我反而要对我好而抱怨),
我想她的诉说,也只是对她当了四十多年正八景的“儿媳妇”的一种倾述。
所以我只报以笑容,或不超过三句的宽慰。毕竟,即便抛开我的角色,命运是无可用语言宽慰的。
有一年包饺子时,婆婆曾经描述说自己去镇里打工,给别人刨鱼,每天20块钱,后来手被泡的受不住,又说镇里的包子铺每天会给做工的人多少钱,工作时间如何,总之听起来是无比心酸的。
我曾跟母亲讲过,母亲感叹的说,让你婆婆来东北吧,我给她找活,保管她不那么累还挣钱。
母亲还说,我这件羽绒服,不穿了,给你婆婆,她会不会嫌弃?
她说这句话、做这件事的时候,俨然救世主的自信,却忘记了自己也只是世间一枚小沙粒。

图解9:不足300人的小村,有两对双胞胎。孩子是最喜欢热闹的。鼓声一响,孩子们飞速跑出来围着看。若干年后,这些长大的孩子,还会记得小时敲鼓的爷爷,还会记得幼时喧闹无忧的春节吗?
自从结婚,每年春节依然延续着委屈,虽然委屈和没结婚时是那样不同。
但是那个小村,尽管我因为各种原因很是抗拒与它的每一次接触,但心里,依然想念它。
我想,等我成母亲、成婆婆、成奶奶的那一日,可以坐在一个明亮暖和的房间,给儿孙准备各种好吃好喝的时候,我终究会怀念这些年,在满是浓烟的黯淡小屋,我过的这些年,和我过这些年的这些人。
一定会怀念的。